|
|
жң¬ж–Үз”ұ жё еҺҝзҪ‘ www.quxian.cn ж•ҙзҗҶжҸҗдҫӣпјҡ
ж ёеҝғжңҹеҲҠжӢ’з»ҷеӯҰз”ҹзҪІеҗҚ еӨҚж—Ұж•ҷжҺҲдёәеӯҰз”ҹдәүзҪІеҗҚж’ӨзЁҝ

2016е№ҙ6жңҲпјҢеӨҚж—ҰеӨ§еӯҰеӣҪйҷ…е…ізі»дёҺе…¬е…ұдәӢеҠЎеӯҰйҷўеүҜж•ҷжҺҲйғ‘зЈҠе’ҢеҗҢеӯҰ们еңЁдёҖж¬ЎеӯҰжңҜдјҡи®®дёҠеҗҲеҪұгҖӮеҸ—и®ҝиҖ…дҫӣеӣҫ
в– еҜ№иҜқдәәзү©
йғ‘зЈҠ
70еҗҺпјҢ2002е№ҙеҮәеӣҪз•ҷеӯҰпјҢе…ҲеҗҺеңЁдәҡеҲ©жЎ‘йӮЈеӨ§еӯҰеҸ–еҫ—зЎ•еЈ«еӯҰдҪҚпјҢзәҪзәҰе·һз«ӢеӨ§еӯҰеҸ–еҫ—еҚҡеЈ«еӯҰдҪҚгҖӮ2009е№ҙеӣһеӣҪпјҢзҺ°д»»еӨҚж—ҰеӨ§еӯҰеӣҪйҷ…е…ізі»дёҺе…¬е…ұдәӢеҠЎеӯҰйҷўеүҜж•ҷжҺҲгҖӮ
в– еҜ№иҜқеҠЁжңә
йғ‘зЈҠе’ҢзЎ•еЈ«з ”з©¶з”ҹеҗҲеҶҷзҡ„дёҖзҜҮи®әж–ҮпјҢиў«еӣҪеҶ…дёҖе®¶ж ёеҝғжңҹеҲҠзәҰзЁҝгҖӮдёҙиҝ‘еҲҠеҸ‘пјҢжңҹеҲҠжҸҗеҮәпјҢйқһеҚҡеЈ«з ”з©¶з”ҹеӨ–пјҢзЎ•еЈ«з ”з©¶з”ҹдёҚиғҪиҒ”еҗҲзҪІеҗҚгҖӮ
еҮ з»ҸжІҹйҖҡжңӘжһңпјҢйғ‘зЈҠеҶіе®ҡпјҡеҸӘиҰҒдёҚи®©еӯҰз”ҹзҪІеҗҚпјҢжҲ‘е°ұеҸӘиғҪж’ӨзЁҝгҖӮ
6жңҲ15ж—ҘжҷҡпјҢйғ‘зЈҠе°Ҷж’ӨзЁҝзҡ„еҶіе®ҡеҸ‘еңЁдәҶжңӢеҸӢеңҲгҖӮзҹӯзҹӯж•°е°Ҹж—¶пјҢ收еҲ°дәҶ341дёӘиөһгҖӮ
вҖңиҝҷд№ҲеӨҡдәәзӮ№иөһпјҢжҒ°жҒ°иҜҙжҳҺиҝҷж ·зҡ„дәӢжғ…еӨӘе°‘дәҶпјҢиҝҷдёҚжҳҜеЈ®дёҫпјҢеҸӘжҳҜдёҖдёӘиҖҒеёҲзҡ„й»ҳи®Өи®ҫзҪ®гҖӮвҖқд»–еёҢжңӣиғҪжҠҠжҜҸдёҖзҜҮеҗҲзҪІзҡ„и®әж–ҮвҖңдҪңдёәеёҲз”ҹеҗҲдҪңзҡ„зҫҺеҘҪеӣһеҝҶвҖқгҖӮ
е…¶е®һйғ‘зЈҠзӣ®еүҚжӯЈеңЁиҜ„жӯЈж•ҷжҺҲиҒҢз§°пјҢиҝҷзҜҮеҺҹжң¬иҰҒеҸ‘иЎЁеңЁж ёеҝғAзұ»жңҹеҲҠдёҠзҡ„и®әж–Үе…·жңүйҮҚиҰҒеҲҶйҮҸгҖӮвҖңиҜ„иҒҢз§°еҸҜд»ҘжҷҡеҮ е№ҙпјҢдҪҶе’ҢеӯҰз”ҹзҡ„жғ…и°Ҡд»ҘеҸҠдҪңдёәеҜјеёҲзҡ„еҺҹеҲҷдёҚиғҪйҖҖи®©гҖӮвҖқ
жңүиҝҮ7е№ҙеӣҪеӨ–з•ҷеӯҰз»ҸеҺҶзҡ„йғ‘зЈҠпјҢиҮід»ҠжҖҖеҝөе’ҢеҜјеёҲзҡ„дәІеҜҶе…ізі»пјҢвҖңеҘ№еңЁеҗ„ж–№йқўз»ҷжҲ‘ж”ҜжҢҒпјҢеҮәй’ұи®©жҲ‘еҸӮеҠ дјҡи®®гҖӮвҖқ
жҜ•дёҡж—¶пјҢйғ‘зЈҠе’ҢеҜјеёҲе‘ҠеҲ«пјҢвҖңеҘ№иҜҙпјҢжҲ‘жҖҺд№ҲеҜ№дҪ пјҢдҪ е°ұжҖҺж ·еҜ№дҪ зҡ„еӯҰз”ҹгҖӮвҖқ
и°Ҳж’ӨзЁҝ
дёҚжӯЈеёёзҡ„дәӢеӨҡдәҶпјҢжӯЈеёёзҡ„дәӢеҸҚеҖ’жҳҫеҫ—еҸҚеёё
ж–°дә¬жҠҘпјҡиҝҷзҜҮи®әж–Үзҡ„з ”з©¶ж–№еҗ‘жҳҜд»Җд№ҲпјҹеӯҰз”ҹеҸӮдёҺдәҶеӨҡе°‘пјҹ
йғ‘зЈҠпјҡиҝҷжҳҜдёҖзҜҮе…ідәҺејҖж”ҫж•°жҚ®зҡ„и®әж–ҮпјҢжҳҜжҲ‘е’ҢеӯҰз”ҹе…ұеҗҢе®ҢжҲҗзҡ„гҖӮ
еңЁиҝҷдёӘ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жҲ‘жӣҙеӨҡең°еҮәжҖқи·ҜгҖҒе®ҡжЎҶжһ¶пјҢеҘ№еҒҡеҹәзЎҖж–ҮзҢ®е·ҘдҪңпјҢ然еҗҺжҲ‘们дёҖиө·и®Ёи®әгҖҒжІҹйҖҡпјҢжңҖеҗҺжҲ‘еҶҚе…Ёйқўи°ғж•ҙгҖҒдҝ®ж”№гҖӮеӯҰз”ҹжҳҜе……еҲҶеҸӮдёҺзҡ„гҖӮ
ж–°дә¬жҠҘпјҡдҪ еңЁд»Җд№Ҳжғ…еҶөдёӢжҸҗеҮәж’ӨзЁҝпјҹ
йғ‘зЈҠпјҡ6жңҲ15ж—ҘжҷҡдёҠпјҢжңҹеҲҠзј–иҫ‘дёҺжҲ‘жІҹйҖҡпјҢиҜҙиҝҳжңүдёҖдёӘиҰҒжұӮпјҢзЎ•еЈ«з”ҹзҡ„еҗҚеӯ—дёҚиғҪеҮәзҺ°пјҢиҮіе°‘жҳҜеҚҡеЈ«з”ҹжүҚиғҪд»ҘеҗҲдҪңиҖ…зҡ„иә«д»ҪзҪІеҗҚгҖӮ
зҪІеҗҚжҳҜеҺҹеҲҷжҖ§й—®йўҳпјҢжҲ‘жҠҠеӯҰз”ҹеҪ“еҗҲдҪңиҖ…жқҘзңӢеҫ…пјҢдёҚиғҪи®©жӯҘпјҢеҸӘиғҪж’ӨзЁҝгҖӮжҲ‘们йғҪжңҹжңӣи®әж–ҮиғҪеӨҹж—©ж—ҘеҸ‘иЎЁпјҢдҪҶжҳҜжҠҠеӯҰз”ҹеҗҚеӯ—жӢҝжҺүпјҢжҲ‘иүҜеҝғдёҠиҝҮдёҚеҺ»гҖӮ
ж–°дә¬жҠҘпјҡ然еҗҺдҪ е°ұеҸ‘дәҶжңӢеҸӢеңҲпјҹ
йғ‘зЈҠпјҡжҲ‘еҪ“ж—¶йқһеёёйҡҫиҝҮгҖӮжҲ‘и·ҹеӯҰз”ҹиҜҙпјҢеҘҪеҘҪеҠӘеҠӣпјҢжҲ‘们е°ұиғҪеҸ‘иЎЁи®әж–ҮгҖӮжҲ‘еңЁеј•еҜјеҘ№иө°дёҠдёҖжқЎжӯЈзӣҙзҡ„еӯҰжңҜд№Ӣи·ҜпјҢжҲ‘жҠҠеҘ№еёҰеҲ°й—ЁеҸЈдәҶпјҢз»“жһңеҜ№ж–№жҠҠй—Ёжү“ејҖпјҡеҜ№дёҚиө·пјҢдҪ ж»ҡеҮәеҺ»пјҢеҸӘжңүиҖҒеёҲеҸҜд»ҘиҝӣжқҘгҖӮ
дёҚжҳҜеӣ дёәиғҪеҠӣгҖҒе“ҒиЎҢпјҢиҖҢжҳҜйҖҡиҝҮеҮәиә«жқҘеҲӨж–ӯдёҖдёӘдәәпјҢиҝҷжҳҜеҫҲдёҚе…¬жӯЈзҡ„зҺ°иұЎгҖӮ
еңЁеӯҰз”ҹиҝҷд№Ҳе№ҙиҪ»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еҸ‘表第дёҖзҜҮи®әж–Үе°ұзў°и§Ғиҝҷз§ҚдәӢжғ…пјҢеҘ№жҢәдёҚдҪҸдәҶжҖҺд№ҲеҠһпјҹдёүи§Ӯеӣ жӯӨйў иҰҶдәҶе‘ўпјҹ
ж–°дә¬жҠҘпјҡдҪ 收еҲ°дәҶжҖҺж ·зҡ„иҜ„и®әпјҹ
йғ‘зЈҠпјҡжңүдәәе°Ҷе…ідәҺжӯӨдәӢзҡ„дёҖзҜҮж–Үз« еҸ‘еҲ°дәҶзӨҫдәӨзҪ‘з«ҷпјҢжҲ‘з•ҷж„ҸдәҶеҫ®еҚҡзҡ„иҜ„и®әгҖӮжңүдәәиҜҙпјҢиҝҷдёӘиҖҒеёҲйғҪдёҚиҜҙжңҹеҲҠеҗҚеӯ—пјҢиӮҜе®ҡжҳҜзј–зҡ„ж•…дәӢпјӣжңүдәәиҜҙпјҢиҖҒеёҲжҖҺд№ҲеҸҜиғҪдёәдәҶи®әж–ҮзҜҮж•°ж”ҫејғеҲҠеҸ‘пјҢеҒҮзҡ„гҖӮ
жҲ‘е“ӯ笑дёҚеҫ—гҖӮдёҚжӯЈеёёзҡ„дәӢеӨҡдәҶпјҢжӯЈеёёзҡ„дәӢжғ…еҸҚеҖ’жҳҫеҫ—еҸҚеёёдәҶгҖӮжңүдәәеҒҡдәҶеҹәжң¬зҡ„гҖҒжӯЈзЎ®зҡ„дәӢжғ…пјҢеҚҙжІЎжңүдәәзӣёдҝЎпјҢиҝҷдёӘзӨҫдјҡз—…еҲ°д»Җд№ҲзЁӢеәҰдәҶпјҹ
ж–°дә¬жҠҘпјҡеӯҰз•ҢеҗҢиЎҢжҖҺд№ҲиҜ„д»·пјҹ
йғ‘зЈҠпјҡжҲ‘е®Ңе…ЁжІЎжңүжғіиҝҮеҗҢиЎҢзҡ„зңӢжі•пјҢжҲ‘и®Өдёәиҝҷж ·еҒҡжҳҜиҖҒеёҲзҡ„дёҖдёӘвҖңй»ҳи®Өи®ҫзҪ®вҖқгҖӮ
жҲ‘зңӢеҲ°еҘҪеӨҡиҖҒеёҲзӮ№иөһпјҢдёҚдјҡжңүиҖҒеёҲз«ҷеҮәжқҘеҸҚеҜ№зҡ„пјҢдҪҶжҳҜжҲ‘еҸҜд»ҘиҜҙпјҢжңүдёҖдәӣиҖҒеёҲжҳҜжІүй»ҳзҡ„гҖӮиҖҢжІүй»ҳжҳҜжңүеҗ«д№үзҡ„гҖӮ
зҺ°еңЁпјҢиҝҷ件дәӢжғ…еј•иө·еҫҲеӨ§и®Ёи®әпјҢе®ғзҡ„зӨҫдјҡд»·еҖје·Із»Ҹи¶…и¶Ҡи®әж–Үжң¬иә«пјҢеқҸдәӢеҸҳеҘҪдәӢгҖӮ
и°ҲжңҹеҲҠзҪІеҗҚ
дёҚзңӢжҜҚйёЎжҳҜи°ҒпјҢиҖҢжҳҜзңӢйёЎиӣӢеҘҪдёҚеҘҪ
ж–°дә¬жҠҘпјҡиҝҷ家жңҹеҲҠдёәд»Җд№Ҳдјҡжңүиҝҷж ·зҡ„иҰҒжұӮпјҹ
йғ‘зЈҠпјҡеңЁжІҹйҖҡдёӯпјҢжҲ‘дәҶи§ЈеҲ°пјҢ他们жҳҜдёәдәҶжқңз»қдәәжғ…зЁҝпјҢжүҚеқҡеҶідёҚи®©еҚҡеЈ«еӯҰеҺҶд»ҘдёӢзҡ„еӯҰз”ҹзҪІеҗҚгҖӮ他们зҡ„еҲқиЎ·жҳҜеҘҪзҡ„гҖӮдҪҶжҳҜиҝҷж ·дёҖеҲҖеҲҮдјҡжҠ‘еҲ¶еӯҰз”ҹзҡ„еӯҰжңҜз§ҜжһҒжҖ§гҖӮ
е…¶е®һиҝҳжңүдёҖз§ҚеҺҹеӣ пјҢжңҹеҲҠзӯүзә§дёҺеҸ‘иЎЁи®әж–Үзҡ„дҪңиҖ…зӣёе…іпјҢдёҖеӨ§е ҶйҷўеЈ«жүҚи§үеҫ—еҫҲй«ҳзә§гҖӮз”Ёиҝҷж ·зҡ„ж ҮеҮҶжқҘиҜ„д»·жңҹеҲҠпјҢд№ҹе°ұйҖјеҫ—жңҹеҲҠдёҚеҫ—дёҚиҝҷж ·йқўеҜ№дҪңиҖ…гҖӮ
дҪҶиҝҷж ·жҖҺд№Ҳйј“еҠұеӯҰжңҜеҲӣж–°пјҹиҝҷдјҡжүјжқҖеӨ©жүҚгҖӮ
6жңҲ20ж—ҘдёҠеҚҲпјҢжңҹеҲҠи·ҹжҲ‘иҜҙпјҢ他们д№ҹеңЁи®Ёи®әжңүжІЎжңүдёҖз§ҚеҠһжі•пјҢж—ўеҸҜд»Ҙжқңз»қдәәжғ…зЁҝпјҢеҸҲиғҪйҒҝе…ҚиҜҜдјӨе№ҙиҪ»зҡ„еӯҰз”ҹгҖӮ
ж–°дә¬жҠҘпјҡжҚ®дҪ дәҶи§ЈпјҢжңүеҫҲеӨҡвҖңдәәжғ…зЁҝвҖқеҗ—пјҹ
йғ‘зЈҠпјҡе“ӘдёӘеңҲеӯҗйғҪжңүеҗ„з§Қеҗ„ж ·зҡ„дәәпјҢжңүе°‘йғЁеҲҶиҖҒеёҲи®©еӯҰз”ҹеҶҷи®әж–ҮпјҢиҖҒеёҲжӢҝжқҘзҪІдёҠеҗҚеӯ—пјҢжҲ–иҖ…еӯҰз”ҹеҗҚеӯ—йғҪдёҚеҮәзҺ°гҖӮ
дёҖдёӘдәәзҡ„дҝ®е…»еҸ–еҶідәҺеҜ№еҫ…жҜ”д»–ең°дҪҚдҪҺзҡ„дәәзҡ„жҖҒеәҰгҖӮеӯҰз”ҹеӨ„дәҺејұеҠҝпјҢдҪ жӣҙиҰҒе°ҠйҮҚд»–пјӣжҠҠд»–зҡ„и®әж–ҮжӢҝиҝҮжқҘзҪІдёҠиҮӘе·ұзҡ„еҗҚеӯ—пјҢиҝҷжҳҜж¬әеҺӢгҖӮжңүжІЎжңүиүҜеҝғе‘ўпјҹжҲ‘и§үеҫ—жҜ”иҫғйҒ—жҶҫгҖӮ
ж–°дә¬жҠҘпјҡдҪ еңЁеӣҪеӨ–з•ҷеӯҰпјҢеӣҪеӨ–жңҹеҲҠжңүиҝҷж ·зҡ„иҰҒжұӮеҗ—пјҹ
йғ‘зЈҠпјҡиҝҷз§ҚиҰҒжұӮжҳҜеӣҪеҶ…зү№жңүзҡ„гҖӮ
еӣҪеӨ–жҳҜеҢҝеҗҚиҜ„е®ЎеҲ¶пјҢдҪңиҖ…е°ҶзЁҝ件жҠ•з»ҷжҹҗдёӘж ёеҝғжңҹеҲҠпјҢжңҹеҲҠзј–иҫ‘иҝӣиЎҢеҲқжӯҘеҲӨж–ӯеҗҺпјҢйҡҗеҢҝдҪңиҖ…姓еҗҚпјҢеҲҶеҲ«еҸ‘йҖҒз»ҷ3еҲ°5еҗҚдёҡеҶ…专家гҖӮ专家дёҚзҹҘйҒ“ж–Үз« дҪңиҖ…пјҢдҪңиҖ…д№ҹдёҚзҹҘйҒ“еҸӮиҜ„зҡ„жҳҜе“ӘеҮ дҪҚ专家гҖӮ
е®ғжҳҜдёҖз§ҚжҜ”иҫғзҗҶжҖ§гҖҒе№ІеҮҖзҡ„жІҹйҖҡгҖӮдёҚд»ҘеҮәиә«еҶіе®ҡи®әж–ҮиҙЁйҮҸпјҢдёҚзңӢжҜҚйёЎжҳҜи°ҒпјҢиҖҢжҳҜзңӢйёЎиӣӢеҘҪдёҚеҘҪгҖӮ
ж–°дә¬жҠҘпјҡдҪ и§үеҫ—иҝҷз§Қе·®ејӮзҡ„еҺҹеӣ жҳҜд»Җд№Ҳпјҹ
йғ‘зЈҠпјҡеӯҰжңҜж–ҮеҢ–зҡ„е·®ејӮйҖ жҲҗдәҶеӯҰжңҜйҒ“еҫ·зҡ„й—®йўҳгҖӮ
еҸҜиғҪжҲ‘们зҡ„дј з»ҹж–ҮеҢ–жҳҜдёҖз§Қзӯүзә§е·®зҡ„ж–ҮеҢ–пјҢиҖҒеёҲи®ӨдёәеӯҰз”ҹең°дҪҚдҪҺпјҢиҝҷж ·жҳҜеә”иҜҘзҡ„гҖӮиҖҢ欧зҫҺең°еҢәзӣёеҜ№е№ізӯүдёҖдәӣпјҢжҳҜеҗҲдҪңзҡ„е…ізі»гҖӮ
иҝҷзӮ№дёҠпјҢжҲ‘еқҡжҢҒеҜ№зҡ„дәӢжғ…пјҡе№ізӯүпјҢе°ҠйҮҚгҖӮж— и®әд»–жҳҜд»Җд№Ҳең°дҪҚпјҢж №жҚ®иҙЎзҢ®еӨ§е°ҸеҶіе®ҡзҪІеҗҚгҖӮ
и°ҲеёҲз”ҹе…ізі»
еёҲз”ҹдёҚжҳҜйӣҮдҪЈе…ізі» иҖҒеёҲиҰҒеӣһеҪ’жң¬иҙЁ
ж–°дә¬жҠҘпјҡеңЁи®әж–ҮзҪІеҗҚж–№йқўпјҢдҪ зҡ„еҜјеёҲжҳҜжҖҺд№ҲеӨ„зҗҶзҡ„пјҹ
йғ‘зЈҠпјҡжҲ‘е’ҢеҜјеёҲжҳҜжӯЈеёёзҡ„еҗҲдҪңе…ізі»гҖӮ
иҜ»еҚҡеЈ«жңҹй—ҙпјҢжңүзҜҮиҜҫзЁӢи®әж–ҮжҳҜжҲ‘зӢ¬з«ӢеҶҷзҡ„пјҢеҜјеёҲз»ҷдәҶдёҖдәӣдҝ®ж”№е»әи®®гҖӮжҢүз…§дёӯеӣҪдәәе°ҠйҮҚиҖҒеёҲзҡ„дј з»ҹпјҢжҲ‘иҜ·иҖҒеёҲеҒҡ第дәҢдҪңиҖ…гҖӮеҜјеёҲиҜҙпјҢжҲ‘еҸӘжҳҜз»ҷдҪ е»әи®®пјҢиҝҷжҳҜдҪ зҡ„ж–Үз« пјҢжҲ‘дёҚиғҪжІҫдҪ зҡ„е…үгҖӮ
жҲ‘еҸ‘иЎЁдәҶеҫҲеӨҡеӣҪйҷ…дјҡи®®зҡ„и®әж–ҮпјҢеҘ№еҮәй’ұи®©жҲ‘еҺ»еҸӮеҠ иҝҷдәӣдјҡи®®гҖӮ
зұ»дјјиҝҷж ·зҡ„дәӢжғ…пјҢеҜ№жҲ‘жҳҜеҫҲеҘҪзҡ„иЁҖдј иә«ж•ҷгҖӮзӯүжҲ‘еҪ“дәҶиҖҒеёҲпјҢжҲ‘д№ҹиҰҒиҝҷж ·еҜ№еӯҰз”ҹгҖӮжҲ‘жҳҜзҗҶжғідё»д№үиҖ…пјҢжҲ‘зӣёдҝЎиҝҷдәӣгҖӮ
ж–°дә¬жҠҘпјҡдҪ еҒҡиҖҒеёҲиҝҷеҮ е№ҙпјҢеҒҡеҲ°дәҶеҗ—пјҹ
йғ‘зЈҠпјҡеҰӮжһңжҳҜеҘҪзҡ„еӯҰжңҜдјҡи®®пјҢжҲ‘дјҡеҮәй’ұжҠҠеӯҰз”ҹ们еёҰдёҠгҖӮжңүдёҖж¬Ўдјҡи®®пјҢжҲ‘еёҰдәҶ4дёӘеӯҰз”ҹпјҢдҪҶеҲ«зҡ„иҖҒеёҲйғҪжІЎеёҰеӯҰз”ҹпјҢжҲ‘们жҳҫеҫ—еӨӘжүҺзңјдәҶпјҢеҗҺжқҘж”№жҲҗиҪ®жөҒеёҰгҖӮ
жҲ‘и·ҹеӯҰз”ҹиҜҙпјҢдҪ иҰҒеҸ‘дәҶеӣҪйҷ…и®әж–ҮпјҢжҲ‘д№ҹиө„еҠ©дҪ еҮәеӣҪгҖӮ
еӯҰз”ҹеҸӮдёҺе®һйӘҢе®Өзҡ„иҜҫйўҳпјҢе“ӘжҖ•жҳҜжң¬з§‘з”ҹпјҢеҸӘиҰҒжӯЈеёёеҸӮдёҺиҜҫйўҳе·ҘдҪңпјҢжҜҸдёӘжңҲйғҪж №жҚ®иҙЎзҢ®жңүдёҖе®ҡйҮ‘йўқзҡ„иЎҘеҠ©пјҢи·ҹеңЁеӨ–йқўе®һд№ зҡ„иЎҘиҙҙдёҖж ·гҖӮ
ж–°дә¬жҠҘпјҡеүҚж®өж—¶й—ҙпјҢеҚҺдёңзҗҶе·ҘеӨ§еӯҰдёҖдҪҚз ”з©¶з”ҹжӯ»дәҺеҜјеёҲиҝқ规ејҖеҠһзҡ„е·ҘеҺӮгҖӮдҪ жҖҺд№ҲзңӢеҫ…иҝҷ件дәӢпјҹ
йғ‘зЈҠпјҡиҝҷжҳҜдёӘжһҒз«ҜжЎҲдҫӢгҖӮ
иҝҷз§Қжғ…еҶөжүӯжӣІдәҶеёҲз”ҹе…ізі»гҖӮеёҲз”ҹе…ізі»дёҚжҳҜйӣҮдҪЈе…ізі»пјҢд№ҹдёҚжҳҜеҲ©з”Ёе’Ңиў«еҲ©з”Ёзҡ„е…ізі»гҖӮ
зҺ°еңЁеӨ§еӯҰйҮҢжҷ®йҒҚжҠҠеҜјеёҲз§°дёәиҖҒжқҝпјҢжҲ‘зҡ„еӯҰз”ҹд№ҹеҸ«жҲ‘иҖҒжқҝгҖӮиҖҒеёҲжҖҺд№ҲиғҪжҲҗиҖҒжқҝе‘ўпјҹиҖҒеёҲиҰҒеӣһеҪ’жң¬иҙЁпјҡжҳҜеӯҰз”ҹзҡ„еј•йўҶиҖ…пјҢиҰҒеј•йўҶеӯҰз”ҹеҫҖеҘҪзҡ„ж–№еҗ‘иө°гҖӮ
ж–°дә¬жҠҘпјҡеңЁдҪ зңӢжқҘпјҢеӣҪеҶ…еӨ–еҜјеёҲе’ҢеӯҰз”ҹзҡ„е…ізі»пјҢе·®ејӮеңЁе“ӘйҮҢпјҹ
йғ‘зЈҠпјҡжҲ‘и§үеҫ—иҝҳжҳҜе№ізӯүе’Ңе°ҠйҮҚгҖӮ
еңЁеӣҪеҶ…пјҢиҖҒеёҲеҜ№еӯҰз”ҹеҘҪдёҖзӮ№пјҢеӯҰз”ҹдјҡи§үеҫ—жҳҜдёҖз§ҚжҒ©иөҗгҖӮиҝҷз§ҚжҒ©иөҗзҡ„еҒҮи®ҫе°ұжҳҜеӣ дёәжҲ‘们жҳҜдёҚе№ізӯүзҡ„гҖӮеӣҪеҶ…жңүдёҖдәӣиҖҒеёҲд№ жғҜжү№иҜ„пјҡдҪ и·ҹжҲ‘дёҚдёҖж ·пјҢжҲ‘е°ұжү№иҜ„дҪ гҖӮ
еңЁзҫҺеӣҪпјҢжҲ‘жӣҙеӨҡең°ж„ҹеҸ—еҲ°еӯҰжңҜдёҠзҡ„е№ізӯүгҖӮжҲ‘еҸҜд»ҘжҢҮеҮәиҖҒеёҲе“ӘйҮҢжІЎжңүжғіе‘Ёе…ЁпјҢеҘ№еҸҚиҖҢдјҡеҫҲйҮҚи§Ҷиҝҷз§Қе·®ејӮеҢ–е’ҢеӨҡе…ғеҢ–пјӣжҲ‘иҰҒжҳҜиҜҙI agreeпјҲжҲ‘еҗҢж„ҸпјүпјҢеҘ№еҸҜиғҪдјҡжңүзӮ№еӨұжңӣгҖӮ
жҲ‘еёҢжңӣеӯҰз”ҹиғҪеӨҹжңүжӣҙеӨҡзҡ„жҖқиҖғпјҢеҹ№е…»д»–зӢ¬з«Ӣз ”з©¶гҖҒзӢ¬з«ӢеҲҶжһҗиғҪеҠӣгҖӮ
ж–°дә¬жҠҘпјҡдҪ и®Өдёәеә”иҜҘеҰӮдҪ•ж”№е–„иҝҷж ·зҡ„зҠ¶еҶөпјҹ
йғ‘зЈҠпјҡиҝҷиҰҒд»Һж•ҙдёӘдҪ“зі»е’ҢеӯҰжңҜзҺҜеўғжқҘеҸҚжҖқпјҢж—ўиҰҒжңүиҮӘеҫӢд№ҹиҰҒжңүд»–еҫӢгҖӮ
иҖҒеёҲеҜ№иҮӘе·ұиҰҒжңүиүҜеҝғдёҠзҡ„зәҰжқҹпјӣе…¶ж¬ЎпјҢж•ҙдёӘеҲ¶еәҰгҖҒдҪ“зі»жңүй—®йўҳгҖӮжҜ”еҰӮжҲ‘иҜҙеҲ°зҡ„жңҹеҲҠж ҮеҮҶй—®йўҳпјҡеҰӮжһңиҜҙеҸ‘иЎЁеӯҰз”ҹзҡ„и®әж–Үе°ұдёҚжҳҜеҘҪжңҹеҲҠпјҢйӮЈдёҚжҳҜжҠҠжңҹеҲҠвҖңйҖјиүҜдёәеЁјвҖқеҗ—пјҹиҝҷдёҚжҳҜдёҖ家жҲ–еҮ 家жңҹеҲҠзҡ„й—®йўҳпјҢжҳҜж•ҙдёӘеӯҰжңҜз•Ңзҡ„й—®йўҳгҖӮ
жүҖд»ҘжҲ‘иҜҙпјҢжҲ‘ж”№еҸҳдёҚдәҶдё–з•ҢпјҢеҸӘиғҪж”№еҸҳиҮӘе·ұгҖӮ
жң¬зүҲйҮҮеҶҷ/ж–°дә¬жҠҘи®°иҖ… е”җзҲұзҗі
(ж–°дә¬жҠҘ)
жң¬ж–Үз»“жқҹпјҢеӨҡи°ўйҳ…иҜ»пјҒ |
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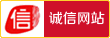 Powered by Discuz! X3.4 © 2008-2024 жё еҺҝзҪ‘ зүҲжқғжүҖжңү иңҖICPеӨҮ2021001069еҸ·-4 е·қе…¬зҪ‘е®үеӨҮ51172502000170еҸ·
жҠҖжңҜж”ҜжҢҒ: е…Ӣзұіи®ҫи®Ў
Powered by Discuz! X3.4 © 2008-2024 жё еҺҝзҪ‘ зүҲжқғжүҖжңү иңҖICPеӨҮ2021001069еҸ·-4 е·қе…¬зҪ‘е®үеӨҮ51172502000170еҸ·
жҠҖжңҜж”ҜжҢҒ: е…Ӣзұіи®ҫи®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