з«Ҙе№ҙжҳҜзҫҺеҘҪзҡ„гҖӮ
з«Ҙе№ҙжҳҜйӮЈд№Ҳзҡ„ж— еҝ§ж— иҷ‘пјҢйӮЈд№Ҳзҡ„еӨ©зңҹж— йӮӘгҖӮе„ҝж—¶е“је”ұзҡ„йӮЈдәӣз«Ҙи°ЈпјҢиҮід»Ҡд»Қжң—жң—дёҠеҸЈпјҢйҹөе‘іеҚҒи¶ігҖӮ
еҮӯи®°еҝҶпјҢжҲ‘жҠ„еҮ ж®өз«Ҙи°Је’ҢеӨ§е®¶еҲҶдә«пјҢжҲ–и®ёеҸҜд»ҘеӢҫиө·еҗҢйҫ„дәәзҡ„йӮЈдәӣз«Ҙе№ҙи¶ЈдәӢпјҢд»ҺдёӯеҲҶдә«еҝ«д№җгҖӮе„ҝж—¶жҳҜеҸЈеӨҙдј е”ұпјҢйҡҫе…Қеӯ—еҸҘжңүиҜҜпјҢжҲ–иҖ…зүҲжң¬дёҚеҗҢпјҢеҠ д№Ӣжңүдәӣж–№иЁҖжҳҜз”Ёж–Үеӯ—иЎЁиҫҫдёҚеҮәжқҘзҡ„пјҢдёәзЎ®дҝқеҺҹж»ӢеҺҹе‘іпјҢжңӢеҸӢ们иҖҒ乡们慢慢еҗҹиҜөгҖӮ
еӨ§йәҰй»„пјҢзӮ’йқўйҰҷпјҢжҠ“жҠҠзӮ’йқўеҗёе©ҶеЁҳгҖӮе©ҶеЁҳеҗёеҲ°жІҹжІҹйҮҢпјҢзӮ’йқўиҝҳеңЁе…ңе…ңйҮҢгҖӮ
й»„иҚҶжЈҚпјҢйЎ¶зҜ®зӣҶпјҢеҜ№й—Ёе“ӘдёӘеҰ№е„ҝжІЎеҫ—з”·дәәгҖӮй»„иҚҶжЈҚпјҢйЎ¶з°ёз®•пјҢеҜ№й—Ёе“ӘдёӘеҰ№е„ҝиҜҘжҲ‘жҺҘгҖӮ
жҘјдёҠзҡ„е®ўпјҢжҘји„ҡзҡ„е®ўпјҢиҰҒеҗ¬иҖҒжқҝеҠһдәӨжҺҘгҖӮиҰҒеұҷеұҺпјҢжңүиҢ…еұҺпјҢиҺ«еҫ…жҘјдёҠж‘Ҷж‘ҠеӯҗгҖӮиҰҒеұҷе°ҝпјҢжңүеӨңеЈ¶пјҢиҺ«еҫ…еәҠдёҠз”»ең°еӣҫгҖӮ
ж•ҷдҪ ж•ҷдҪ е°ұж•ҷдҪ пјҢжҠҠдҪ еӨ№еҲ°иЈӨиЈҶйҮҢгҖӮдёүеӨ©дёүеӨңдёҚж”№дҪ пјҢзһҺпјҲиҷұпјүеӯҗиҷјиҡӨе’¬жӯ»дҪ гҖӮ
еӨ§жңҲдә®,иө°еІ©дёҠпјҢ е“Ҙе“Ҙиө·жқҘеӯҰи”‘еҢ гҖӮе°ҸжңҲдә®,иө°жІҹеә•пјҢе«Ӯе«Ӯиө·жқҘзәійһӢеә•гҖӮ е©Ҷе©Ҷиө·жқҘи’ёзіҜзұі. зіҜзұіи’ёеҫ—е–·е–·йҰҷ, жү“иө·й”Је„ҝжҺҘ姑еЁҳ, 姑еЁҳжҺҘдёӢжІі, ж Ҫй«ҳжўҒ. й«ҳжўҒдёҚз»“зұҪ, ж ҪиҢ„еӯҗ, иҢ„еӯҗдёҚејҖиҠұ. ж ҪеҶ¬з“ң, еҶ¬з“ңдёҚй•ҝжҜӣ, ж ҪзәўиӢ•. зәўиӢ•дёҚзүөи—Ө, йҘҝжӯ»жІіеә•дёӨ家дәәгҖӮ
дёүеҚҒе„ҝжҷҡдёҠеӨ§жңҲдә®пјҢиҙјеЁғеӯҗиҝӣеұӢеҒ·ж°ҙзјёгҖӮиҒӢеӯҗеҗ¬еҲ°ж°ҙеңЁе“ҚпјҢзһҺеӯҗиө·жқҘж‘ёжЈ’жЈ’гҖӮзҷһеӯҗиө·жқҘжү“з”өжЈ’пјҢи·ӣеӯҗиө·жқҘж’өдёҖи¶ҹгҖӮ
еј жү“й“ҒжқҺжү“й“ҒпјҢжү“жҠҠеүӘеӯҗйҖҒе§җе§җгҖӮе§җе§җйҖҒеҲ°жЎҘи„ҡжӯҮпјҢжЎҘи„ҡжңүдёӘд№ҢжўўиӣҮпјҢжҠҠжҲ‘иҖіжңөеӨ№дёӘзјәгҖӮжқҖдёӘзҢӘе„ҝиЎҘдёҚеҖ’пјҢжқҖдёӘзүӣе„ҝиЎҘеҚҠжҲӘгҖӮ
жҺЁзЈЁж‘ҮзЈЁпјҢжҺЁдёӘзЈЁе„ҝз»ҶдёҚиҝҮпјҢзӮ•дёӘе·ҙе„ҝйҰҷдёҚиҝҮгҖӮе–«еҚҠиҫ№пјҢз•ҷеҚҠиҫ№пјҢеҰҲеҰҲж”ҫеҲ°жһ•еӨҙиҫ№пјҢиҖ—е„ҝжӢ–еҲ°зҒ¶й—ЁеүҚпјҢзҢ«е„ҝжӢ–еҲ°ең°еққиҫ№пјҢй№һе„ҝеҸјеҲ°жІійӮЈиҫ№пјҢеҫ—е„ҝе•°е—¬пјҢеҫ—е„ҝе•°е—¬гҖӮ
йҳійӣҖеҸ«е”ӨжқҺиҙөйҳіпјҢжңүй’ұиҺ«и®ЁеҗҺеӨҙеЁҳгҖӮеүҚеЁҳжқҖйёЎз•ҷйёЎи…ҝпјҢеҗҺеЁҳжқҖйёЎз•ҷйёЎиӮ пјҢжҠұеҲ°жҹіж ‘е“ӯдёҖеңәгҖӮ
иҜҙзҷҪиҜҙзҷҪе°ұиҜҙзҷҪпјҢиҜҙиө·зҷҪжқҘдәҶдёҚеҫ—гҖӮдёүеІҒеҲ°ж№–еҚ—пјҢеӣӣеІҒеҲ°ж№–еҢ—пјҢж№–еҚ—ж№–еҢ—зңҹй—№зғӯгҖӮжҘјдёҠзқҸзһҢзқЎпјҢдјёжүӢж‘ёеҲ°еӨ©иҖҒзҲ·гҖӮеӨңеЈ¶зӮ–и…ҠиӮүпјҢйҰҷеҫ—иҝҮдёҚеҫ—гҖӮйјҺзҪҗз…®жҜӣй“ҒпјҢзүҷйҪҝе•ғдёҚзјәгҖӮйёӯе„ҝжү‘иҝҮжІіпјҢж·№жӯ»дёғе…«зҷҫгҖӮйә»йӣҖйЈһеҲ°зүӣиғҢдёҠпјҢеҺӢеҫ—ж°”йғҪеҮәдёҚеҫ—гҖӮжҺҗжӯ»дёӘз»ҝиҡҠеӯҗпјҢжөҒдәҶеҚҠжЎ¶иЎҖгҖӮзҒҜиҚүеҒҡзәӨзҙўпјҢдёҖеӨ©жӢүеҲ°й»‘гҖӮжү“еүҜй“Ғй“ҫеӯҗпјҢжүҜжҲҗдёӨеҚҠжҲӘгҖӮ
и°ңиҜӯзҜҮ
е°Ҹж—¶еҖҷз»ҸеёёзҢңи°ңиҜӯгҖӮ
йӮЈдәӣи°ңиҜӯдёҚдҪҶжө…жҳҫжҳ“жҮӮпјҢиҖҢдё”иЁҖиҜӯиҜҷи°җгҖҒзІ—дҝ—пјҢеҫҖеҫҖи®©дәәеҝҚдҝҠдёҚзҰҒгҖӮйӮЈж—¶дҫҜжҲ‘们йғҪжҳҜе°ҸеұҒеӯ©пјҢдёҚжҮӮеҫ—д»Җд№ҲжҳҜиүәжңҜпјҢд»Җд№ҲжҳҜж¬ЈиөҸпјҢеҸӘи§үеҫ—еҘҪзҺ©гҖӮз…һжңүд»ӢдәӢең°зј зқҖеӨ§дәәзҢңпјҢе°‘дёҚдәҶеңЁе°ҸеұҒеӯ©е ҶйҮҢжҳҫж‘Ҷжҳҫж‘ҶпјҢд№ҹиҮӘжңүдёҖд»Ҫд№җи¶ЈгҖӮдәә们еңЁеҠіеҠЁз”ҹжҙ»дёӯеҲӣйҖ дәҶиҝҷдәӣи°ңиҜӯпјҢиҮід»ҠиҝҳжҳҜз¬ҰеҗҲвҖңйӣ…дҝ—е…ұиөҸвҖқдёҖиҜҚзҡ„гҖӮ
й«ҳи„ҡжқҶпјҢйј“зңјзқӣпјҢзҷҪеӨ©жҷҡдёҠйғҪеңЁзҒ°еӨҙеӣ°вҖ”вҖ”зҒ«й’ігҖӮ
дёӨжқЎзҷҪзӢ—пјҢиө°еҲ°жәӘеҸЈпјҢеҗ¬еҲ°ж°ҙеҗјпјҢе°ұеҫҖеӣһиө°вҖ”вҖ”鼻涕гҖӮ
еҚҠеІ©дёҖдёӘжҹҙпјҢзңӢеҲ°еҸҲеңЁеҠЁпјҢжҗ¬еҸҲжҗ¬дёҚжқҘвҖ”вҖ”зүӣе°ҫе·ҙгҖӮ
зў—еҸЈеҸЈйӮЈд№ҲеӨ§пјҢзў—еҸЈеҸЈйӮЈд№ҲеңҶпјҢиЎ—дёҠд№°дёҚеҲ°пјҢд№ЎйҮҢз”ЁдёҚе®ҢвҖ”вҖ”зҠҒеҸЈгҖӮ
з©әзӯ’ж ‘е„ҝз©әзӯ’жЎ пјҢз©әзӯ’ж ‘е„ҝејҖзҷҪиҠұпјҢз»“й»‘жһңпјҢжҺЁзҷҪйқўпјҢзӮ•й»‘е·ҙвҖ”--иҚһеӯҗгҖӮ
иҝңзңӢдёҖжү’зүӣеұҺпјҢиҝ‘зңӢдёҖдёӘзҢҙеӯҗпјҢжҲ‘еҺ»жҸҗд»–иғҢеӢҫпјҢд»–жқҘе’¬жҲ‘й”Өеӯҗ----еӨңеЈ¶гҖӮ
дёҖдёӘйӣҖе„ҝпјҢзҲ¬дёҠжЎҢе„ҝпјҢжҲ‘еҺ»жӢүд»–йӮЈе°ҫе·ҙпјҢд»–жқҘе’¬жҲ‘йӮЈеҳҙе·ҙвҖ”вҖ”з“ўзҫ№гҖӮ
дёӨеҸЈе„ҝдёҖеӨҙеӣ°пјҢеӣ°еҲ°еӣ°еҲ°е°ұеҸ‘жҖ§пјҢеҸ‘жҖ§е°ұеҸүеҚЎпјҢеҸүеҚЎе°ұж”’еҠІвҖ”вҖ”зӯ·еӯҗгҖӮ
жёёжҲҸзҜҮ
еӣһеҝҶиө·е„ҝж—¶еҒҡиҝҮзҡ„йӮЈдәӣжёёжҲҸжҙ»еҠЁпјҢеҫҲжңүи¶Је‘іе„ҝеҫҲеҘҪ笑гҖӮеҰӮиө°зӢ—еҚөеқЁпјҢиө°еұұе„ҝпјҢиө°д№“гҖӮеҰӮдёўжүӢз»ўе„ҝпјҢеҰӮи·із»іжү“жҜҪиҝҮ家家зӯүзӯүпјҢеӨ§е®¶йғҪеҫҲзҶҹжӮүпјҢйғҪзҹҘйҒ“гҖӮ
и—ҸзҢ«пјҡд№ҹеҸ«вҖңиәІзҢ«зҢ«вҖқпјҢе°Ҹж—¶еҖҷеҒҡеҫ—жңҖеӨҡзҡ„жёёжҲҸе°ұжҳҜиәІзҢ«зҢ«гҖӮдёҖзҫӨе°Ҹеӯ©е„ҝиҒҡйӣҶеңЁдёҖиө·пјҢе…¶дёӯдёҖдёӘе°Ҹеӯ©е„ҝејҜи…°еј“иғҢпјҢе…¶дҪҷзҡ„е°Ҹеӯ©е„ҝдјёеҮәеҸіжӢіпјҢдҫқж¬ЎеҸ ж”ҫеңЁд»–иғҢдёҠпјҢйӮЈдёӘе®ҲзӘқи’ҷзңјзқӣзҡ„гҖҒзЁҚеӨ§дёҖзӮ№е„ҝзҡ„е°Ҹеӯ©е„ҝпјҢеҸЈйҮҢе”ұзқҖвҖңж–‘ж–‘зӮ№зӮ№пјҢжў…иҠұйІңиүіпјҢиөӣиҝҮеҗӣеӯҗпјҢе°Ҹдәәи’ҷи„ёвҖқпјҢдёҠдёӢжқҘеӣһж•°жӢіеӨҙпјҢеҪ“жңҖеҗҺдёҖдёӘеӯ—иҗҪеҲ°и°ҒпјҢи°Ғе°ұжҳҜ第дёҖдёӘи’ҷи„ёжүҫзҢ«зҢ«зҡ„дәәгҖӮе°Ҹеӯ©е„ҝ们еӣӣж•ЈејҖеҺ»пјҢиҮӘжүҫең°ж–№йҡҗи—Ҹиө·жқҘпјҢи¶ҒжүҫзҢ«зҢ«зҡ„дёҚжіЁж„Ҹе°ұи·‘еӣһзӘқйҮҢпјҲи’ҷи„ёйӮЈе„ҝпјүеҺ»пјҢеҸ«вҖңеҪ’зӘқе„ҝвҖқгҖӮжүҫзҢ«зҢ«зҡ„жІЎжңүйҖ®еҲ°зҢ«е„ҝпјҢеҸҲ继з»ӯзҺ©дёӢдёҖиҪ®пјҢйҖ®еҲ°и°Ғи°Ғе°ұиҜҘжҺҘжӣҝи’ҷи„ёжүҫзҢ«зҢ«е„ҝдәҶгҖӮ
иҖҒй№°жҠ“йёЎпјҡдёҖдёӘе°Ҹеӯ©е„ҝжү®иҖҒй№°пјҢдёҖдёӘе°Ҹеӯ©е„ҝжү®жҜҚйёЎгҖӮдёҖзҫӨе°Ҹеӯ©е„ҝжӢҪзқҖжҜҚйёЎиЎЈиҘҹиҝһжҲҗдёІпјҢиәІеңЁжҜҚйёЎиә«еҗҺгҖӮзӢЎзҢҫзҡ„иҖҒй№°еҚғж–№зҷҫи®Ўең°иҰҒжҚүе°ҸйёЎпјҢжҜҚйёЎеј ејҖеҸҢжүӢпјҢеӢҮж•ўең°жӢҰжҲӘиҖҒй№°пјҢдҝқжҠӨиҮӘе·ұзҡ„еӯ©еӯҗпјҢдёҖдёІе°Ҹеӯ©е„ҝеӨ§е‘је°ҸеҸ«пјҢе·Ұж‘ҮеҸіж‘ҶпјҢж¬ўеЈ°еҸ«еЈ°дёҚж–ӯпјҢдёҚдәҰд№җд№ҺгҖӮ
жү“еҳЈе„ҝпјҡеңЁе°ҸйҷўзҹіеққйҮҢи·қзҹіеқҺе„ҝпјҲйҳ¶жІҝпјүзәҰ4вҖ”вҖ”5зұіеӨ„пјҢз”ЁдёҖеқ—е°ҸзҹіеӨҙж”Ҝиө·дёҖеқ—е№іж»‘е№ІеҮҖзҡ„й•ҝж–№еҪўзҹіжқҝе„ҝпјҢзәҰ30еқЎеәҰпјҢжҳҜжёёжҲҸзҡ„ж»‘иЎҢи·‘йҒ“гҖӮеҸӮзҺ©е„ҝзҡ„е°ҸжңӢеҸӢеҗ„иҮӘеҮҶеӨҮдёҖжһҡеӨ§й“ңй’ұжҲ–й“ңеңҶпјҢй“ңе…ғдёҖиҲ¬зӣҙеҫ„жңү3е…¬еҲҶжҲ–4е…¬еҲҶгҖӮеңЁжІЎжңүй“ңй’ұжҲ–й“ңеңҶзҡ„ж—¶еҖҷд№ҹеҸҜд»Ҙз”ЁиҮӘж•ІиҮӘзЈЁзҡ„з“ҰзүҮеҳЈе„ҝпјҢдҪҶйҒ“е…·еҝ…йЎ»жҳҜз»ҹдёҖзҡ„гҖӮ规еҲҷжҳҜз”ЁеҳЈе„ҝиҫ№зјҳж•ІиҝҮзҹіжқҝе„ҝпјҢеҖҹйӮЈеқЎеәҰжәңж»ҡеҗ‘еүҚпјҢжңҖйЎ¶зә§зҡ„жҳҜеҳЈе„ҝж–ңз«ӢеңЁйҳ¶жІҝзҹіеқҺе„ҝдёҠпјҢз§°д№ӢдёәвҖңжҢӮзҘһиҫ№е„ҝвҖқпјҢз”ұд»–жңҖе…ҲжҺ·й’ұе„ҝгҖӮжҺ·й’ұе„ҝе°ұжҳҜз«ҷзӣҙиә«еӯҗдёҚејҜи…°пјҢзһ„еҮҶеҗҺз”ЁиҮӘе·ұзҡ„еҳЈе„ҝжҺ·еҮәеҺ»ж•ІжңҖиҝ‘зҡ„еҳЈе„ҝпјҢжҺ·дёӯдәҶе°ұжү“д»–дёҖдёӘжүӢжқҝе„ҝпјҢдёҚдёӯе°ұиҜҘз”ұд»–еҺ»жҺ·еҲ«дәәдәҶгҖӮеҰӮжһңжҳҜеҳЈе„ҝи·іиө·жқҘжҺ·дёӯзҡ„пјҢеҸ«вҖңжҗҒдәҢдёҚеҖјй’ұвҖқпјҢиҷҪжү“дёҚжҲҗжүӢжқҝе„ҝпјҢдҪҶеҸҜд»Ҙ继з»ӯжҺ·гҖӮ
жҠұиӣӢпјҡжҳҜжҲ‘们乡дёӢеңҹиҜқпјҢвҖңжҠұвҖқе°ұжҳҜвҖңеӯөеҢ–вҖқзҡ„ж„ҸжҖқпјҢжҳҜз”·еӯ©еӯҗ们зҺ©зҡ„гҖӮйҡҸдҫҝжҚЎдёүдёӘз –еқ—зҹіеқ—з“Ұеқ—йғҪиЎҢпјҢж”ҫдёҖе Ҷе„ҝпјҢжҠұиӣӢзҡ„дәәи¶ҙдјҸеңЁең°дёҠпјҢдјёзӣҙдёҖжқЎеҸіи…ҝдҪңжҠӨиӣӢзҠ¶гҖӮж—Ғиҫ№зҡ„дәәеЈ°дёңеҮ»иҘҝпјҢиҷҡе®һе…јжңүи¶ҒжңәеҒ·иўӯжҠўд»–зҡ„иӣӢгҖӮд»–дјёзӣҙзҡ„йӮЈжқЎеҸіи…ҝе°ұжҳҜз”ЁжқҘжү«иҚЎеҒ·иӣӢдәәзҡ„гҖӮиў«д»–жү«дёӯпјҢйӮЈд»–е°ұи§Јж”ҫдәҶпјҢе°ұиҜҘдҪ еҺ»жҠұиӣӢдәҶгҖӮд»–зҡ„иӣӢиў«еҒ·е…үдәҶд»–е°ұ继з»ӯи¶ҙеңЁйӮЈйҮҢпјҢжҺҘзқҖзҺ©з¬¬дәҢиҪ®гҖӮ
з ҚеҸүпјҡжңүзӮ№е„ҝзұ»дјјдәҺж–—иҚүпјҢжҳҜиғҢиҚүиғҢзҜјеүІиҚүзҡ„еӯ©еӯҗеңЁйҮҺеӨ–зҺ©зҡ„гҖӮжүҫдёҖдёӘеҸ‘дёүж №жһқдё«зҡ„жЎҗеӯҗж ‘жһқз ҚжҲҗдёүи§’еҸүпјҢеҠӣжүҖиғҪеҸҠпјҢж‘Ҷеҫ—и¶Ҡиҝңи¶ҠеҘҪгҖӮеҲ’дёҖжқЎзәҝпјҢз«ҷеңЁзәҝеӨ–з”©еҮәй•°еҲҖз ҚеҖ’йӮЈдёӘеҸүе°ұиөўдёҖжҠҠиҚүгҖӮ
ж–№иЁҖзҜҮ
ж–№иЁҖпјҢйЎҫеҗҚжҖқд№үпјҢең°ж–№иҜӯиЁҖжҳҜд№ҹгҖӮжё еҺҝж–№иЁҖпјҢд№Ўе‘іе„ҝеҚҒи¶ігҖӮиҜҙжқҘжң—жң—дёҠеҸЈпјҢзӢ¬е…·е·қдёңзү№иүІгҖӮдҪҶжҜ•з«ҹжҳҜд№ЎиЁҖдҝҡиҜӯпјҢж–Үеӯ—жңӘеҝ…иғҪиЎЁиҫҫе®ҢзҫҺпјҢд№ҹеҸӘжңүи°ҷзҶҹжң¬ең°ж–№иЁҖиҖ…иҮӘзҹҘе…¶йҹіпјҢиҮӘжҳҺе…¶ж„ҸпјҢиҮӘйҶүе…¶йҹөпјҢд№җеңЁе…¶дёӯгҖӮ
еңҹз”ҹеңҹй•ҝпјҢиё©жё еҺҝеұұең°д№ӢзҒөж°”пјҢйҘ®жё еҺҝдә•жіүд№Ӣз”ҳйңІпјҢдёҠиҫҲиЁҖдј пјҢд№Ўе…ҡжёІжҹ“пјҢд№Ўйҹійҡҫж”№гҖӮзӨҫдјҡеңЁеҸ‘еұ•пјҢж–ҮжҳҺеңЁиҝӣжӯҘпјҢжңүдәӣеңҹиҜқдҪ дёҚжғіж”№д№ҹжІЎеҫ—ең°ж–№з”ЁдәҶгҖӮеҰӮжҙӢжІ№жҙӢзўұжҙӢзҒ«д№Ӣзұ»пјҢд»ҺеүҚжҠҠйҰҷзҡӮеҸ«вҖңиғ°и„ӮжІ№вҖқпјҢжҒҗжҖ•жІЎжңүеӨҡе°‘дәәжғіеҫ—иө·дәҶгҖӮеҶҷдёӘгҖҠз«Ҙжө·жӢҫи¶ЈгҖӢд№Ӣж–№иЁҖзҜҮпјҢеҶҷеҮ жқЎж–№иЁҖеҮәжқҘеӨ§е®¶еӣһе‘іеӣһе‘іпјҢжқғеҪ“йҶ’зһҢзқЎгҖӮ
еҠӘеҠӣжҺЁе№ҝжҷ®йҖҡиҜқпјҢиө°еҮәжё еҺҝй—ҜеӨ©дёӢгҖӮ
е—Ҝе“Әпјҡе“ҰгҖӮ е“Ұе—¬пјҡжңүзӮ№е„ҝжғӢжғң гҖӮ еҠіж…°пјҡи°ўи°ў гҖӮ йә»жәңпјҡеҠЁдҪңеҝ« гҖӮ жң—еҹғпјҡжҖҺд№ҲеӣһдәӢ гҖӮи§Ғиҫ№пјҡдёҺдәәж–№дҫҝгҖӮ жӯӘжқҶе„ҝпјҡеҫҲеҮ¶гҖӮ е‘ўжӯӘгҖҒйӮЈжӯӘпјҡиҝҷдёӘгҖҒйӮЈдёӘгҖӮ жҒҒеҹғгҖҒжөӘеҹғпјҡиҝҷж ·гҖҒйӮЈж ·гҖӮ жҒҒе„ҝдёӘгҖҒй—Ёе„ҝдёӘпјҡд»ҠеӨ©гҖҒжҳҺеӨ©гҖӮ е‘ўеҸ·е„ҝгҖҒжӢүеҸ·е„ҝпјҡиҝҷйҮҢгҖҒйӮЈйҮҢгҖӮ еҰ–иүіе„ҝпјҡжңүзӮ№е„ҝеҮәж јзҡ„ж„ҸжҖқгҖӮ жҮөеӯҗеӣўпјҡжҢҮе№ҙе№јдёҚжҮӮдәӢгҖӮе°–и„‘еЈіпјҡиў«жҲҙз»ҝеёҪеӯҗгҖӮ й—әе„ҝеӯҗпјҡжңӘе©ҡз”ҹеӯҗгҖӮ иҙјеЁғеӯҗпјҡе°ҸеҒ· гҖӮ жЈ’иҖҒдәҢпјҡеңҹеҢӘгҖӮ еҚ–зҳӘзҳӘеҸЈпјҡе“ӯгҖӮ жү“жӯ»е·ҙй”ӨпјҡдёҚдёҺдәәж–№дҫҝгҖӮ ж·ЎиҜқе©Ҷе„ҝпјҡе°Ҹ姑еӯҗгҖӮ зӢ—е„ҝйә»жұӨпјҡеҫҲжқӮд№ұгҖӮ жҜӣз„ҰзҒ«иҫЈпјҡжҖҘиәҒгҖӮ жөҒдәҢйә»жұӨпјҡжӢ–жіҘеёҰж°ҙгҖӮ жұ—е·ҙж°ҙжөҒпјҡжұ—ж°ҙеӨҡгҖӮ йј»ж·ӢеҸЈж°ҙпјҡжөҒ鼻涕пјҢжөҒеҸЈж°ҙгҖӮ еӮ»зҡ®ж—Ҙж’®пјҡжҶЁж ·гҖӮ еҚ–йә»иұҢиұҶе„ҝпјҡжҺүзңјжіӘгҖӮ жү“е–Ҹеҗ§е ӮпјҡиҜҙиҜқдёҚеҲ©зҙўгҖӮ еҗ№зүӣгҖҒе—Ёзҡ®гҖҒеҶІеЈіеӯҗпјҡиҜҙеӨ§иҜқгҖӮ и·¶еҢҚзҲ¬пјҡж‘”и·ӨгҖӮ еЎһеұҒзңје„ҝпјҡеҗғйҘӯгҖӮ еҗғе“Ҹз¬јеҝғиӮәпјҡеҗғзӢ¬йЈҹгҖӮ еұҷз—ўе·ҙеӯҗпјҢжү“ж ҮжһӘпјҡжӢүиӮҡеӯҗгҖӮ жІҷзүӣпјҢиҚүзӢ—пјҢзӘқзҢӘпјҡжҜҚз•ңгҖӮ зүөзӘқпјҢиө°иҚүпјҢйқ жҳҘпјҡзүІз•ңдәӨй…ҚгҖӮ еұҺеұҒзңје„ҝжӢүжІҷзҡ„пјҡиҺ«еҗҚе…¶еҰҷгҖӮ еҒ·еҶ·йҘӯзҡ„пјҢеһ«еұҒиӮЎзҡ„пјҡжҲҸз§°е°ҸеҸ”еӯҗгҖӮжү’зҒ°дҪ¬е„ҝпјҢзғ§зҒ«дҪ¬е„ҝпјҡжҲҸз§°еЁ¶дәҶе„ҝеӘіеҰҮзҡ„з”·дәәгҖӮ
зі—дәӢзҜҮ
иҜҙиҜҙе„ҝж—¶йӮЈдәӣзі—дәӢпјҢйӮЈдәӣе“Ҳе®қе„ҝдәӢгҖӮ
и°ғзҡ®жҚЈиӣӢзҡ„еӯ©еӯҗйғҪжңүйӮЈд№ҲзӮ№е„ҝе°ҸиҒӘжҳҺпјҢе№јж—¶е‘ўпјҢеӨ§дәә们иҜҙ他们жҳҜвҖңжҮөеӯҗеӣўе„ҝвҖқдёҚжҮӮдәӢгҖӮжңүдёӘеҚҒеІҒе…«еІҒзҡ„е°ұеҸ«д»–们вҖңеӨ©жЈ’й”Өе„ҝвҖқгҖҒеҸ«д»–们вҖңеӯҪйҡңжЈ’е„ҝвҖқгҖҒеҸ«д»–们вҖңе“Ҳе®қе„ҝвҖқгҖӮе…¶иЎҢдёәеұһдәҺвҖңеӨ©еҫ—еҫҲвҖқгҖҒжҲ–вҖңеӯҪеҫ—еҫҲвҖқгҖҒжҲ–вҖңе“Ҳеҫ—еҫҲвҖқпјҢиҝҷдәӣж·ҳ气鬼让家й•ҝ们既е–ңдё”жҖ’пјҢеҫҲжҳҜж— еҘҲпјҢе°‘дёҚеҫ—жү“дәҶжүӢжқҝе„ҝеҸҲжү“еұҒиӮЎгҖӮ
йҡ”еЈҒдәҢжҜӣе’ҢдёүеЁғжҳҜвҖңдёӨдёӘеҢ…и°·дёҚйӣ¶еҚ–вҖқзҡ„дёҖеҜ№е°Ҹдјҷдјҙе„ҝпјҢдёүеЁғжҜ”дәҢжҜӣеӨ§еҮ дёӘжңҲиҰҒзҳҰе°ҸдёҖдәӣеҚҙжңәзҒөдёҖдәӣпјҢдәҢжҜӣиҷҪвҖңдә”еӨ§дёүзІ—вҖқжҶЁеӨҙжҶЁи„‘дҪҶе‘ұ唧еҸҜзҲұпјҢдё”з»Ҹеёёж¬әиҙҹдёүеЁғпјҢд»ӨдёүеЁғеҮәдәҶжҙӢзӣёеҸҲеҸ—е°ҪдәҶиӢҰеӨҙе„ҝгҖӮжІЎеҠһжі•е‘ҖпјҢжү“дёҚиҝҮд»–еҷ»гҖӮдҪҶжҜ•з«ҹжҳҜе°Ҹеӯ©е„ҝдёҚи®°д»ҮпјҢ鼻涕зңјжіӘжІЎжҸ©е№ІеҮҖе°ұеҸҲе’ҢеҘҪдәҶгҖӮдёүеЁғиҒӘжҳҺе‘ҖпјҢиЎЁйқўдёҠе¬үзҡ®з¬‘и„ёе”Ҝе”ҜиҜәиҜәпјҢеҚҙеңЁеҝғзңјйҮҢзӯ–еҲ’зқҖдјәжңәжҠҘеӨҚ гҖӮ
йӮЈе№ҙеӨҙеӨ§йӣҶдҪ“з”ҹдә§пјҢеңЁиҫ№иҝңең°еқ—е„ҝйғҪеӨҮжңүз®Җжҳ“зІӘеқ‘пјҢй—Іж—¶е ҶзӮ№е„ҝе№ІзІӘд»Җд№Ҳзҡ„пјҢиҖҒеӨ©дёӢйӣЁеӮЁж°ҙжіЎзқҖгҖӮиҝҷеӨ©дәҢжҜӣдёүеЁғйғҪжқҘиҝҷзүҮеұұжўҒж”ҫзүӣпјҢдәҢжҜӣйҘӯйҮҸеӨ§еҸҲиҖҒжҳҜжӢүеұҺпјҢжІЎйӮЈд№ҲеӨҡ讲究пјҢдәҢжҜӣеј“зқҖдёӘе…үеұҒиӮЎи№ІеңЁйӮЈзІӘеқ‘иҫ№дёҠгҖӮдёүеЁғжҡ—е–ңпјҢеҝғжғіиҝҷжңәдјҡз»ҲдәҺжқҘдәҶгҖӮжҠұиө·дёҖдёӘзҹіеӨҙеқЁеқЁпјҢйӣ„иөіиөіең°з«ҷеңЁзІӘеқ‘еҗҺеқЎеқҺдёҠпјҢйј“иө·зҳҰи„ёиӣӢе„ҝдёҠж¶Ёзәўзҡ„и…®её®еӯҗпјҢдјёзӣҙйӮЈж №е„ҝй»„иҠұжңӘејҖиҲ¬зҡ„жҢҮеӨҙе„ҝпјҢй—®дәҢжҜӣжҖ•дёҚжҖ•д»–пјҢй—®дәҢжҜӣиҝҳж•ўдёҚж•ўеҶҚжү“д»–пјҢеҰӮжһңиғҶж•ўеҸҚжҠ—е°ұжҠҠзҹіеӨҙжү”иҝӣзІӘеқ‘йҮҢгҖӮдәҢжҜӣиҝҷдёӘжҖҘе‘ҖпјҢжҸҗиЈӨе„ҝи·‘жҳҜжқҘдёҚеҸҠдәҶпјҢеҪ“жҖӮеҢ…е„ҝеҗ—еҸҲдёҚз”ҳеҝғпјҢзЎ¬ж’‘еҗ§д№ҹдёҚеҗҲйҖӮгҖӮзңӢйӮЈдёүеЁғжһ¶еҠҝжҳҜзңҹиҰҒжү”зҹіеӨҙзҡ„пјҢеј„дёҖиә«зІӘиҮӯеҸҜдёҚеҘҪзҺ©е„ҝгҖӮдәҢжҜӣйј»еӯҗдёҖвҖңе“јвҖқпјҢйқһеёёдёҚжғ…ж„ҝең°з»“жқҹдәҶиҝҷд»Ҫе°ҙе°¬гҖӮ
иҝҷдәҢжҜӣд№ҹдёҚжҳҜзңҒжІ№зҡ„зҒҜпјҢе“Әж ·е“ҲдәӢе„ҝеҒҡдёҚеҮәжқҘгҖӮдёүеЁғ家иҮӘз•ҷең°иҫ№иҫ№е„ҝдёҠдёҖж №еҚ—з“ңи—Өе„ҝпјҢз»“дёӘеҚ—з“ңеҰӮеҚҮеӯҗиҲ¬еӨ§пјҢжҒ°еҘҪи·әеңЁдәҢжҜӣ家иҮӘз•ҷең°иғҢеқҺеқҺзҡ„зҹіеў©дёҠпјҢйқ’жҙјжҙјең°й•ҝеҠҝе–ңдәәгҖӮдәҢжҜӣжӮ„жӮ„ең°еҒ·еҮә家йҮҢеүҘзӘқз¬Ӣз”Ёзҡ„иҚүеҸ¶еҪўе°ҸеҲҖпјҢз»•йӮЈеҚ—з“ңиӮҡзңје„ҝдёҖжәңзғҹжҺҸдәҶдёӘжӢіеӨҙиҲ¬еӨ§дёҖеқЁз“ңиӮүдёӢжқҘ пјҢйӮЈзІҳе‘је‘јзҡ„з“ңж¶ІиҝҳеҶ’жіЎе„ҝе‘ўгҖӮеҶҚз”ЁжүӢжҠ еҮәдәӣз“ңз“ӨиҗҪдёӘе°Ҹеқ‘пјҢжү’иҗҪиЈӨеӯҗпјҢжҠҠдёӘеңҶеў©еў©е„ҝзҡ„еұҒиӮЎеҮ‘иҝ‘йӮЈе°ҸжҙһпјҢеңЁйӮЈдёӘе№ҙд»ЈпјҢжҲ–и®ёжҳҜиҝ„д»ҠдёәжӯўпјҢдәҢжҜӣз»қеҜ№жҳҜиҝҷдё–з•ҢдёҠ第дёҖдёӘдә«еҸ—е…Ёзҗғ第дёҖжөҒе“ҒзүҢпјҢ第дёҖжөҒеҚ«жөҙи®ҫж–ҪпјҢеңЁжңҖзҺҜдҝқзҡ„пјҢжңҖеҺҹз”ҹжҖҒзҡ„马桶дёҠй…Јз•…ж·Ӣжј“ең°еҝ«ж„ҹдёҖеӣһзҡ„第дёҖдәәгҖӮзӣ–дёҠжҺҸиҗҪзҡ„йӮЈеқЁз“ңпјҢеҘҮиҝ№иҲ¬ең°зІҳе’ҢдёҠдәҶгҖӮзӣҙеҲ°еҚ—з“ңжҲҗзҶҹпјҢдёүеЁғеҰҲеҰҲиғҢеӣһеҸҲеӨ§еҸҲиҖҒзҡ„гҖҒеңҶжәңжәңзҡ„гҖҒй»„зҒҝзҒҝзҡ„гҖҒйј“иө·з“Јз“Је„ҝзҡ„гҖҒеҗҺжқҘиў«жү”жҺүдәҶзҡ„йӮЈдёӘеӨ§еҚ—з“ңеҗҺпјҢдәҢжҜӣеҫҲжҳҜжӯүж„Ҹең°е‘ҠиҜүз»ҷдёүеЁғпјҢд»–жҳҜеҰӮдҪ•еҰӮдҪ•ең°дёәеҚ—з“ңж–ҪиҝҮиӮҘпјҢиҖҢдё”йҡҗзһ’иҮід»Ҡзҡ„е°Ҹз§ҳеҜҶгҖӮ
иҝҷдёӨе®қиҙқд№ҹеӨҹжҠҳи…ҫзҡ„пјҢжҚўзқҖиҠұж ·йҖ—д№җеӯҗгҖӮйӮЈе№ҙд»ЈжҲ–и®ёеҚҒеІҒе…«еІҒйғҪиҝҳжІЎдёҠеӯҰе Ӯе‘ўпјҢиҖҒдәәиҜҙзҡ„вҖңеҸҚжӯЈдәҢеӨ©йғҪжҳҜжү“зүӣиғҜиғҜпјҢиҜ»дёҚиҜ»д№ҰеҸҲе•·е“ҺвҖқгҖӮжҲҗеӨ©иҰҒд№ҲзүөдёӘзүӣе„ҝпјҢиҰҒд№ҲиғҢдёӘиҚүиғҢзҜ“е„ҝгҖӮе°‘дёҚдәҶзҲ¬дёҠз«№еӯҗжҺҸдёӘйә»йӣҖиӣӢе„ҝпјҢжҗ…жө‘ж»ҡзүӣеҮјзҡ„ж°ҙж‘ёдёӘйұје„ҝиҷҫзұіе„ҝгҖӮе…үдёӘи„ҡжқҝе„ҝпјҢиҠұдёӘи„ёеҢ…е„ҝпјҢз”·еӯ©еӯҗеҳӣпјҢжҳҜйӮЈеҚғзғҰеҚғзғҰзҡ„гҖӮ
дёҖж¬ЎдёүеЁғиө°дәәжҲ·еӣһжқҘпјҢдәҢжҜӣ笑咧咧зҡ„иҝҺжҺҘдёүеЁғгҖӮеҸӘи§ҒдёүеЁғеҸіжүӢжҢЈи„ұиЈӨи…°еёҰд»ҺеұҒиӮЎйӮЈе„ҝжҸЎдёӘжӢіж ·жҠҪеҮәжқҘпјҢжҚӮдҪҸдәҢжҜӣйј»еӯҗпјҢдё«ејҖжүӢжҢҮпјҢдёҖиӮЎејәзғҲзҡ„еұҒиҮӯе‘іеҶІиҝӣдәҢжҜӣйј»еӯ”гҖҒзҒҢе…ҘдәҢжҜӣе–үз®ЎгҖҒиҗҪеҲ°дәҢжҜӣиӮ иғғйҮҢгҖӮдәҢжҜӣйӮЈдёӘжҒЁе‘Җ пјҢд»…дёӨеӨ©дёҚи§ҒпјҢиҝҳжңүзӮ№е„ҝжҖӘжғіжҖӘжғізҡ„пјҢеҲҡи§Ғйқўе°ұжҸҚд»–д№ҹдёҚеҗҲйҖӮпјҢзңҹдёӘеә”дәҶвҖңеҘҪеҝғжІЎеҘҪжҠҘвҖқе“ҰгҖӮ
дәҢжҜӣдёҖи§ҒдҫҝзҹҘпјҢзӨје°ҡеҫҖжқҘпјҢзӣёдә’еӣһ敬пјҢд№ҹж— дј‘ж— жӯўең°жү©ж•Ји”“延пјҢз«Ҙи¶ЈеёёжңүпјҢ笑иҜқеёёз•ҷгҖ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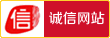 Powered by Discuz! X3.4 © 2008-2024 жё еҺҝзҪ‘ зүҲжқғжүҖжңү иңҖICPеӨҮ2021001069еҸ·-4 е·қе…¬зҪ‘е®үеӨҮ51172502000170еҸ·
жҠҖжңҜж”ҜжҢҒ: е…Ӣзұіи®ҫи®Ў
Powered by Discuz! X3.4 © 2008-2024 жё еҺҝзҪ‘ зүҲжқғжүҖжңү иңҖICPеӨҮ2021001069еҸ·-4 е·қе…¬зҪ‘е®үеӨҮ51172502000170еҸ·
жҠҖжңҜж”ҜжҢҒ: е…Ӣзұіи®ҫи®Ў